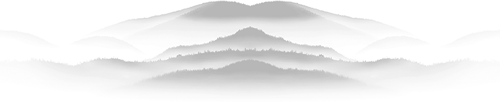永嘉場在龍灣 龍灣潭在永嘉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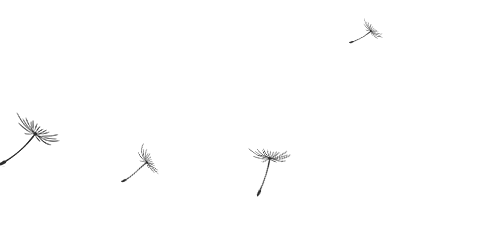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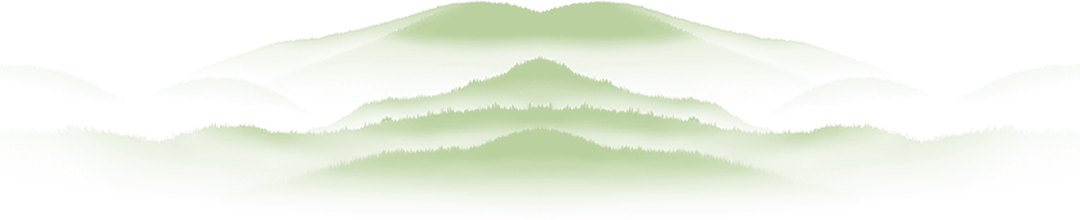
“朝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。宋明以來,趙建大、王瓚、張璁……一個個永嘉場農家子弟改變了自己的人生命運,為激勵后學發憤圖強治學有為樹立了良好的榜樣,同時在內外互動交流中極大地影響著整個溫州經濟、文化的發展。本期,潘偉光先生引經據典,講述永嘉場的名人軼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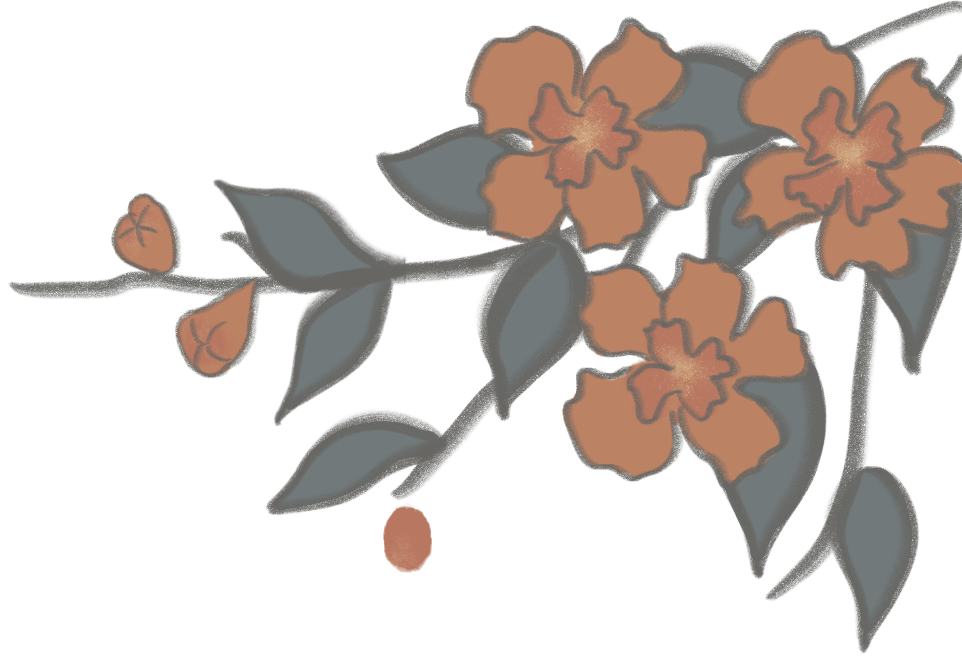

永嘉場在龍灣 龍灣潭在永嘉
文 / 潘偉光

“海坦沙漲,溫州出相”,歷史早已實證;“永嘉場在龍灣,龍灣潭在永嘉”,事實毋庸質疑。既是宰相又是榜眼的陳宜中曾撰《潘氏族譜原序》文中說“余鄉濱海,堪輿家嘗謂吾甌諸龍會于羅峰”,可見陳宜中是“吾甌諸龍會于羅峰”的預言家(羅峰是張璁之號),冥冥之中實有天意抑或巧合乎?
我友網名“水墨”說,現海坦山嶺背已鏟平,其下江涂打樁變公路,無沙可漲了。溫州再無出相了,最多出“副相”。我笑說,副相也是相,就是出個省部級也是值得慶賀的,其祖墳上也會依稀可見縷縷青煙。只不過,青煙的高度濃度可能與官位的高低成一定的比例,反正“祖墳冒煙”從此取代了“海坦沙漲”,皆是百年難遇的吉兆祥瑞。

大凡民間故事傳說,是當不得真的。如張閣老智斗何文淵,漢劉秀逃難快活嶺之類,大家往往大多是付之一笑,不把它當碼事的。正如想了解三國歷史,須看《三國志》的,但偏偏有人把《三國演義》當歷史讀。永嘉場的民間傳說也很多,很多人也信以為真,如傳說鄭老爺的“神船”曾送王叔果王叔杲兄弟上京趕考,新城底人大多深信不疑,還每年組織人員拿著豬頭“三牲”、花紅蠟燭諸物件,到海濱沙北的“鄭老爺殿”(俗稱“上殿”,跟位于海濱建新村的“東甌王廟”俗稱下殿相對應)祭拜,恭敬有加。事后還說,溫州永強機場(今龍灣國際機場)選址在沙村,難道沒有一點關系?!又如明代沙北的一位新娘出嫁七甲,路過清冥殿時猝死,傳說被清冥爺納妾了。于是沙北周氏信眾每年也同樣照例給予上香祭祀禮遇,仿佛走親拜年似的。
據當地人王靖岳先生回憶,每年正月初十,永昌堡也有抬佛節(抬鄭老爺與東甌王)。嘉靖四十一年(1562),戚繼光援溫,倭退閩海。王氏義師將領王叔杲決定上京會試,但溫州舉子已組隊赴京會試路上。王叔杲決定走海路趕上,許愿請鄭老爺保其一帆風順,果真風和日麗,順風順水,趕上考期,得中進士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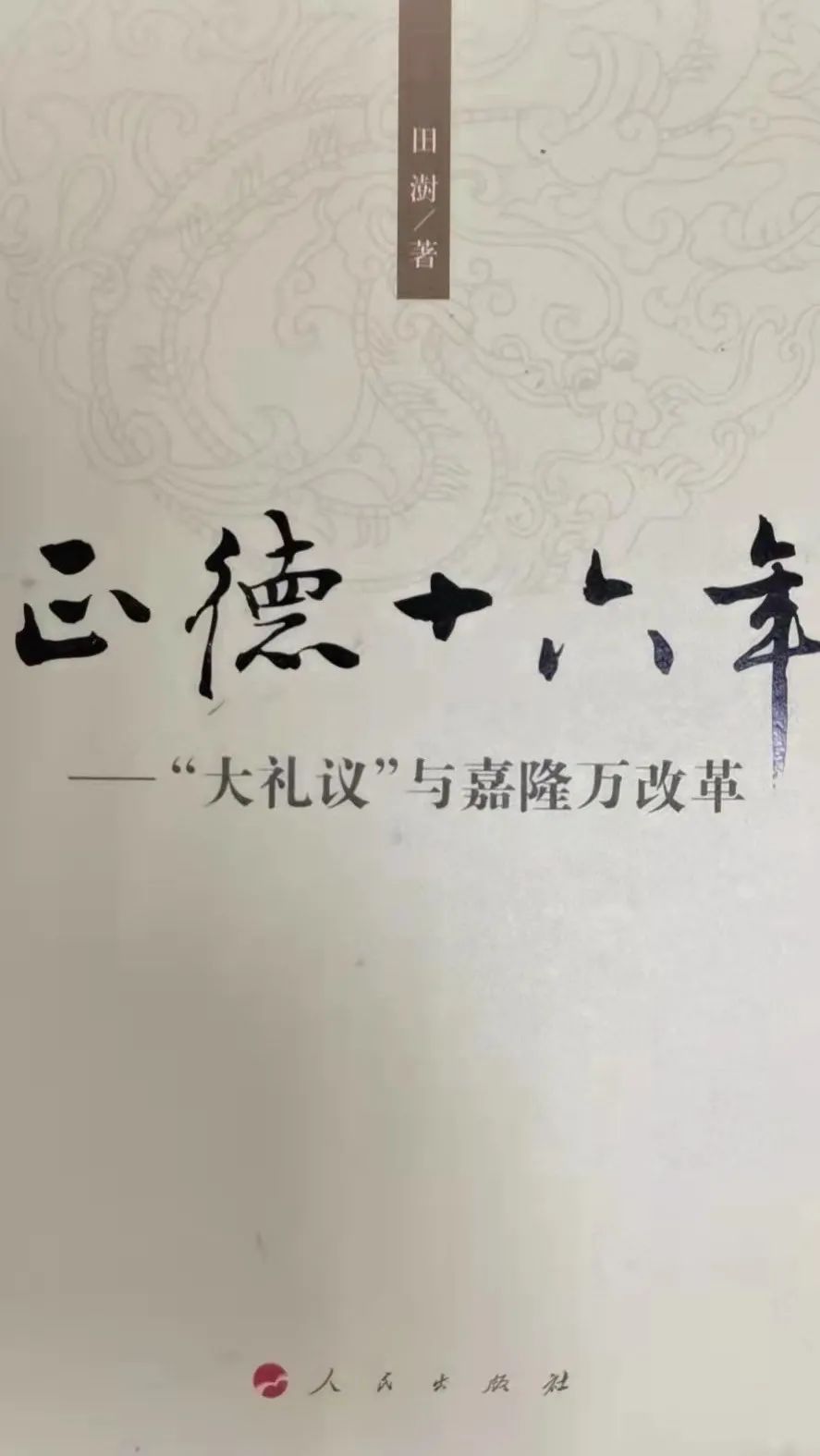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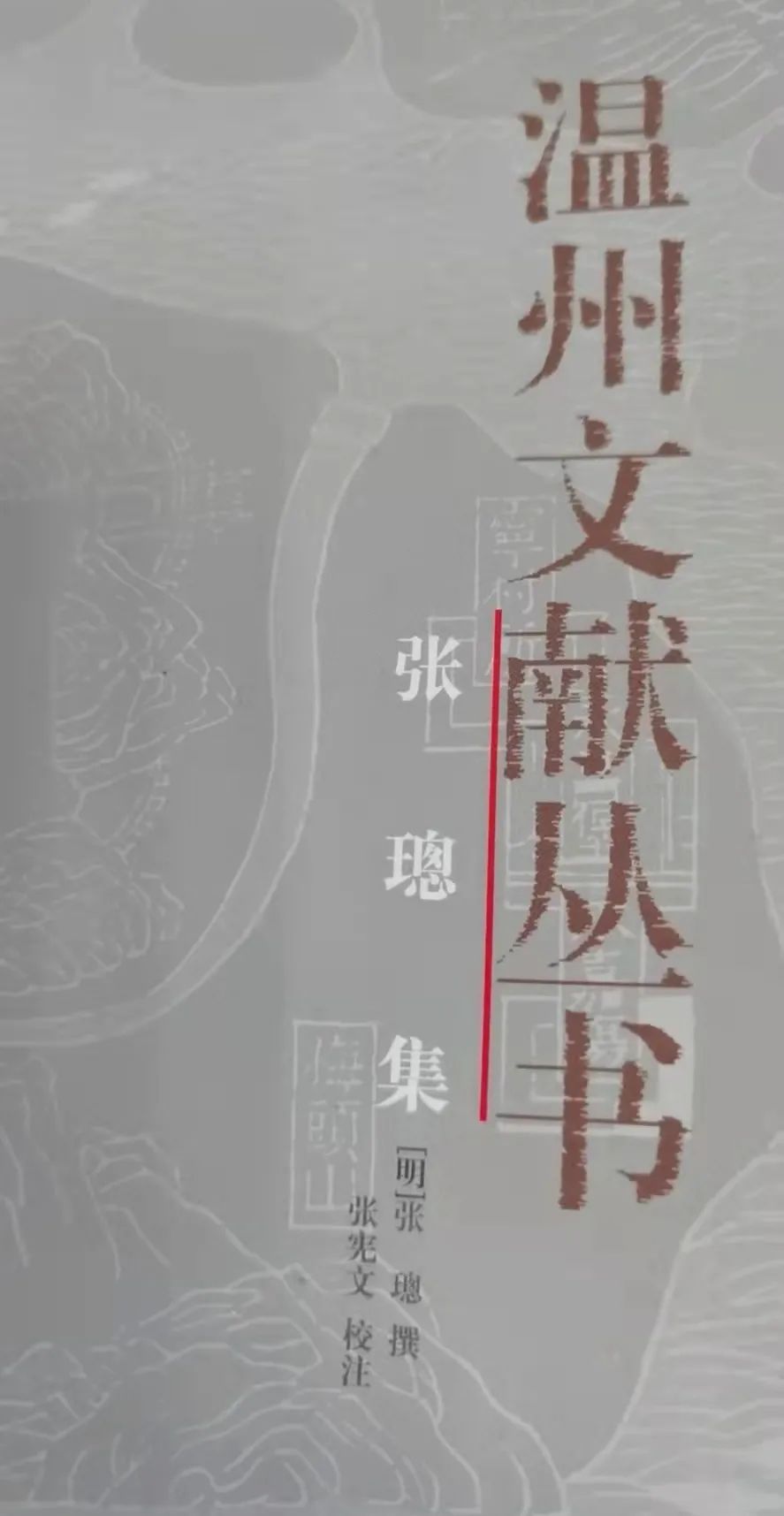
嘉靖八年(1529)首輔張璁為廖紀所作的《送廖尚書歸休》,是廖紀一生寫照:
先生歸去易,志士立身艱。
心跡清於水,聲名重似山。
片言侵宰輔,多旨動天顏。
聖主尊耆舊,胡為獨放還。

而有意思的是廖紀(1455-1532)的號偏偏又是“龍灣”,度娘說他系北直隸河間府東光縣(今河北省滄州市東光縣)人,祖籍在今海南省萬寧市禮紀鎮三星村一帶(原屬陵水縣),民間稱作“廖天官”,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、吏部尚書,是海南史上兩個進入朝廷權力中樞的一品重臣之一,也是海南“十大廉吏”之一。
史載,位于瑤溪的“貞義書院”系明正德十三年(1518)張璁為舉人時建。初名羅峰書院,有屋三間,園五畝,堂名“敬義”,用以授徒講學。嘉靖七年(1528),世宗為之敕建“敬一亭”“抱忠堂”而更新之,賜名“貞義書院”,在溫州方言中,敬義貞義音近。另外,因避諱而賜名之“孚敬茂恭”,是非有“弗敬貌恭”之諧音暗喻不得而知,可知者乃張璁時進諍言,“伴君如伴虎”,惹得龍顏一時不悅,以致四黜四起,比之鄧小平之三起三落猶有過之。

一個人成名后,便自然有許多玄虛之說,如不是說相有異稟,便是說命有宿根,似非如此附麗,不足以顯其殊異。尤其是星相之說,相傳已久,其言禍福,偶或應驗,故人多信之。惟嚴謹學者寧愿按張璁之立身行事,說他可貴可敬之處,不在于形相命運,而在于他一生赤膽忠心,奮斗不懈。此處暫且不表,待另撰文續之。
三都普門張維庚說張璁“豬肚臉”,威嚴有余親和不足,讓人望而生畏,所以“撤鎮守內官”,朝中原先那些飛揚跋扈的宦官從此噤如寒蟬小心翼翼畢恭畢敬。一旦一個人冷如冰霜不言茍笑,一臉嚴肅喜怒不形于色,這可能就是傳說中“六親不認”的面相。確實,他一生廉潔從政嫉惡如仇,任人唯賢,絕不任人唯親,對自己家人尤其嚴厲,從不給政敵反對黨一點把柄一絲借口。其對兒子遜志、遜業如此,對外甥親友也是如此,如王激、項喬、叔果、叔杲等。這與嘉靖后期的首輔嚴嵩相比之下天差地別,嚴嵩滿臉堆笑謙恭有加,逢人都是“正月初一送元寶,只講好”,與太監內臣狼狽為奸沆瀣一氣,而且“一人得道雞犬升天”,不僅兄弟姐妹子女親否不問,而且內舅外舅、姐夫妹夫、阿哥阿妹、阿狗阿貓,只要認親孝敬,都有一頂或大或小的烏紗帽戴戴。所以,曠代名著《水滸傳》《金瓶梅》中高俅、西門慶諸色人等,其實都是取了宋人名諱、穿了宋代官服的嚴嵩同時代的人,不過那個時代用了假身份證沒人追究罷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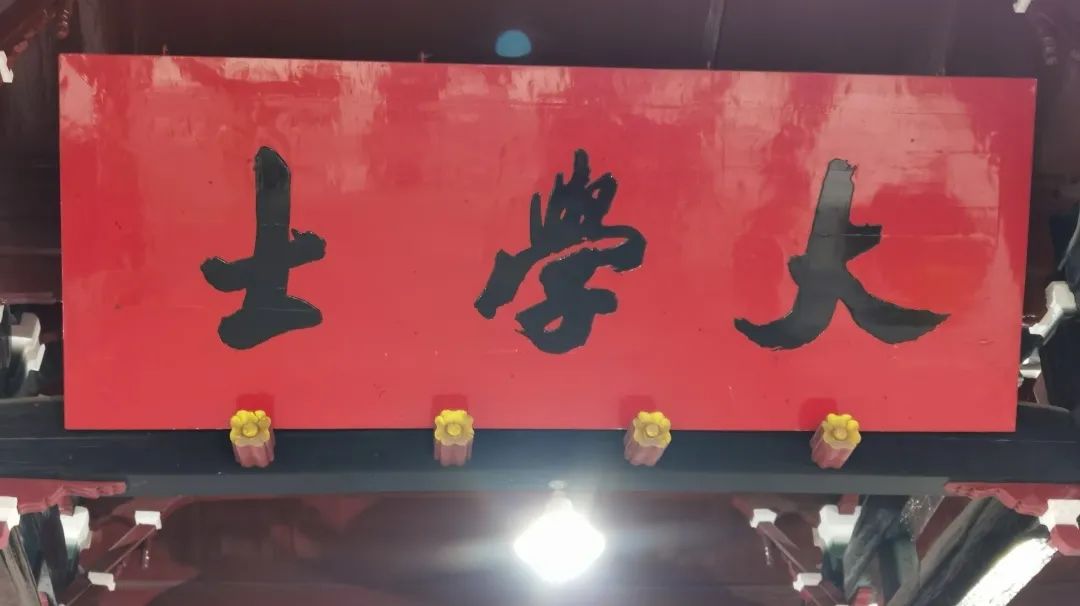
魯迅曾言一部“二十四史”,猶帝王將相之家譜。而其中記載的人物自受精那一刻起,往往屢有異項征兆出現,如紅光滿室,天將祥瑞,夢中怪異,種種不一而足。撰述人的目的很明確,此人物有別于凡夫俗子,即使不是真龍天子,也是星神下凡,兼具人神兩種身份。
明王同軌的《耳談笑增》記載了張閣老的一則故事:
永嘉山中有虎逐人,其人登大樹而虎守其下。忽張文忠孚敬腹懷文忠,自母家歸,天微雨,憩坐虎脊上,複取履擦泥其皮。樹上人見之,膽落。已,人群至,虎去,追問母何由坐虎背。母曰:“巨石也。”次日,屬人察樹下,何巨石之有?已而生文忠,人已知貴有征矣。
史載張璁出生于明憲宗成化十一年(1475),其時其父張昪年已四十九,生母謝氏(注:鶴陽謝氏為永嘉望族)年亦四十二。就是說,張璁出生時,父母都已年近半百,所以出現難產癥狀而驚怖椿萱,何況此前已育有三子,“將棄之”,就不難理解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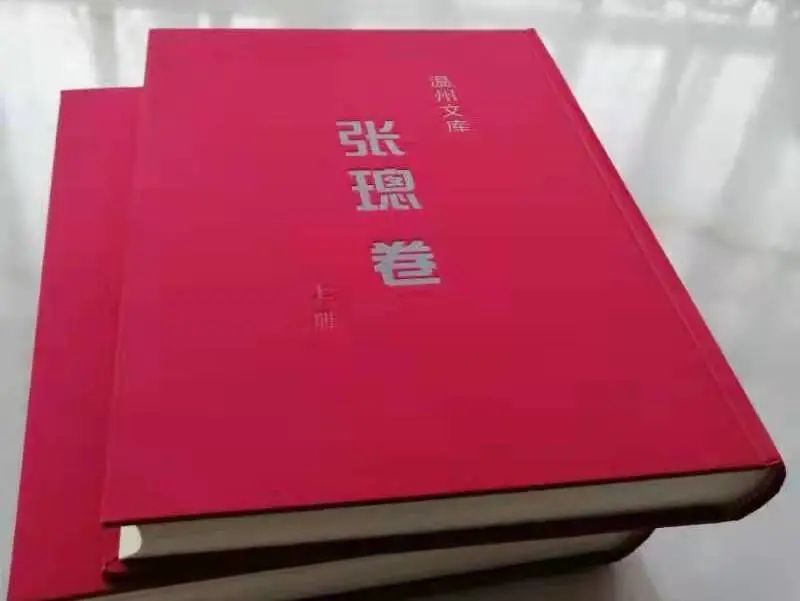
天降大任于斯人,總有幾番磨難與挫折。此時,二位偉大的女性對張璁起了關鍵性的作用。一是文忠女兄——
文忠公之始生,父母以日薄,懼罔克見少子成立,欲弗舉。恭人內不忍,乃緣物為讖家語曰:“養則當大起吾族。”父母悅而收之。已而,母謝夫人卒,公且幼。恭人泣曰:“夫道屬,人道析,茲非吾弟乎?吾弟,吾弟之也。由是撫愛倍至,令二子與同學業,卒以成器,入相今天子。(明趙大佑《封太恭人張氏墓志銘》)
后張族果應文忠一人而顯。
二是季氏大嫂——乃璁之同里下垟街老北橋人,年二十歸璁之伯兄為妻室。當時“將棄”情形下,幸虧其嫂“故請育之,因扶我鞠我,乳我哺我。我嫂也實我乳母也。”(《北門季氏家乘序》)又,《普門張氏家乘》載張璁之子張遜業《冢伯母季太孺人墓志銘》云:“先考少師公始生也,謝夫人以艱育故,將欲不舉,太孺人奇其啼聲而代育焉。”
所以,張璁發達后,對此耿耿于懷,視同親母,如同包拯之伺候其嫂。“誰言寸草心,板得三春暉”,后來致仕歸田時,特地拜登季氏之祠,爰建板恩坊以褒揚其嫂季氏,彰其“幽嫻性成,孝慈田植”之節德。

弘治七年(1494)20歲,他考取秀才,學官驚其論,曰:“此子異日不特以文鳴世,立朝氣節殆不可量也。”
另,明劉萬春《守官漫錄》中說張璁到無錫去拜訪邵泉齋一事。邵泉齋,何許人也?邵寶,字國賢,號泉齋,別號二泉居士。官至南京禮部尚書。邵當場試一對“月白風清,鶴淚一聲山寂寂”,張即對云“云行雨施,龍飛萬里海茫茫",邵聽后“大器之,遂登第,未久拜相,蓋此公氣魄已從詩對見之。”
張璁從20歲考秀才到24歲中舉人,一路折桂如囊中取物,但考進土,19年間7次赴考皆鎩羽而歸。心灰意懶退而講學,人生似乎從此不起波瀾。此時,又有一個關鍵的人在關鍵時刻講了關鍵的話——“以此三載成進士,又三載當驟貴”(《明史.張璁傳》)“成進士,即與人主若一身,聲蜚海內,位極人臣,于世無比。” (《張太師世家》)聽君一席話,勝讀十年書,何況希望在即,區區三年而已。這話在張璁在考試與就業的糾結之際無異于醍醐灌頂,真是憑空傾下冰雪水,劈開兩爿頂陽骨。又如晴空霹靂一聲響,從此驚醒夢中人。恰恰令人驚詫的是居然應驗了,豈不是人生命數?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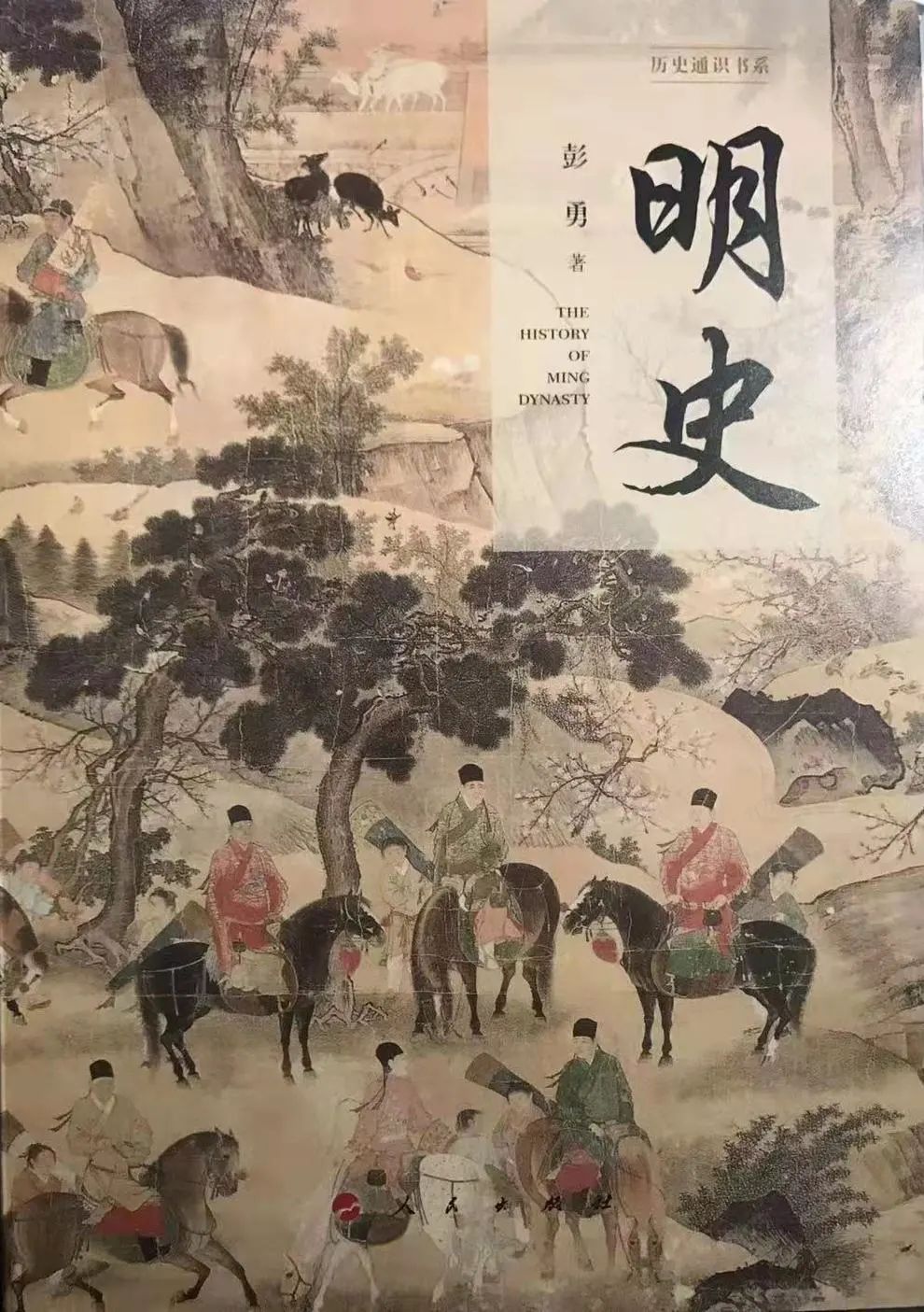
明沈德符《萬歷野獲編》卷七“內閣”記載,可與上互證:
永嘉張文忠老於公車,欲就選,而山陰人蕭鳴鳳止之,謂其支幹當正位首相;蕭自言星命亦當至二品。其後張果大拜;時蕭以副使擅笞知府廢罷,張思前言,且感其意,起用之,欲引為正卿以符前說。蕭官至布政而卒,亦二品也。
其實有關張璁星命當貴的傳說在明人筆記中比比皆是。如清勞大與《甌江逸志》也有同樣的記載:
光山王相為禦史,判高郵,有精鑒。時張羅峰文忠以落第候除,相一見奇之,謂曰:“子有異表,他日所就,奚止科第?”因厚貽之。羅峰既貴,上疏曰:“王相以忠鯁蒙誣,宜恤。”詔贈光祿寺少卿。
又明王兆云《湖海搜奇》記載:
羅峰久困禮闈,將謁選於銓曹。蕭靜庵素以臺輔期之,力沮不從,複危言動之,乃止。三年,複入試,試畢,題詩於席舍曰:“月色團團照舉場,河光片片落天章。風雲交會人初散,星斗芒寒夜未央。敢向人心論用舍?直於吾道蔔行藏。至公堂上焚香在,吾力猶能系紀綱。”是年逐登第,不出十年即拜相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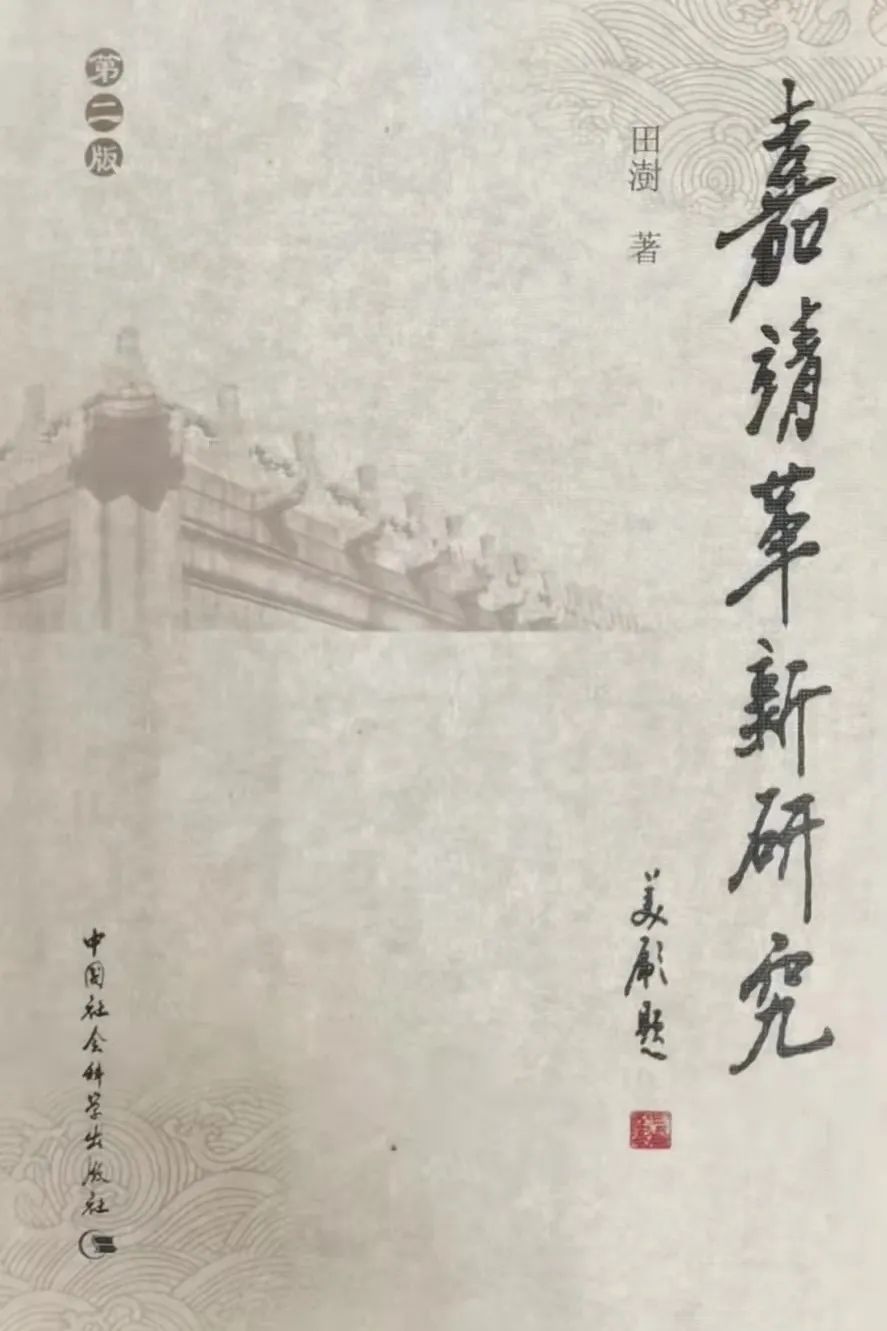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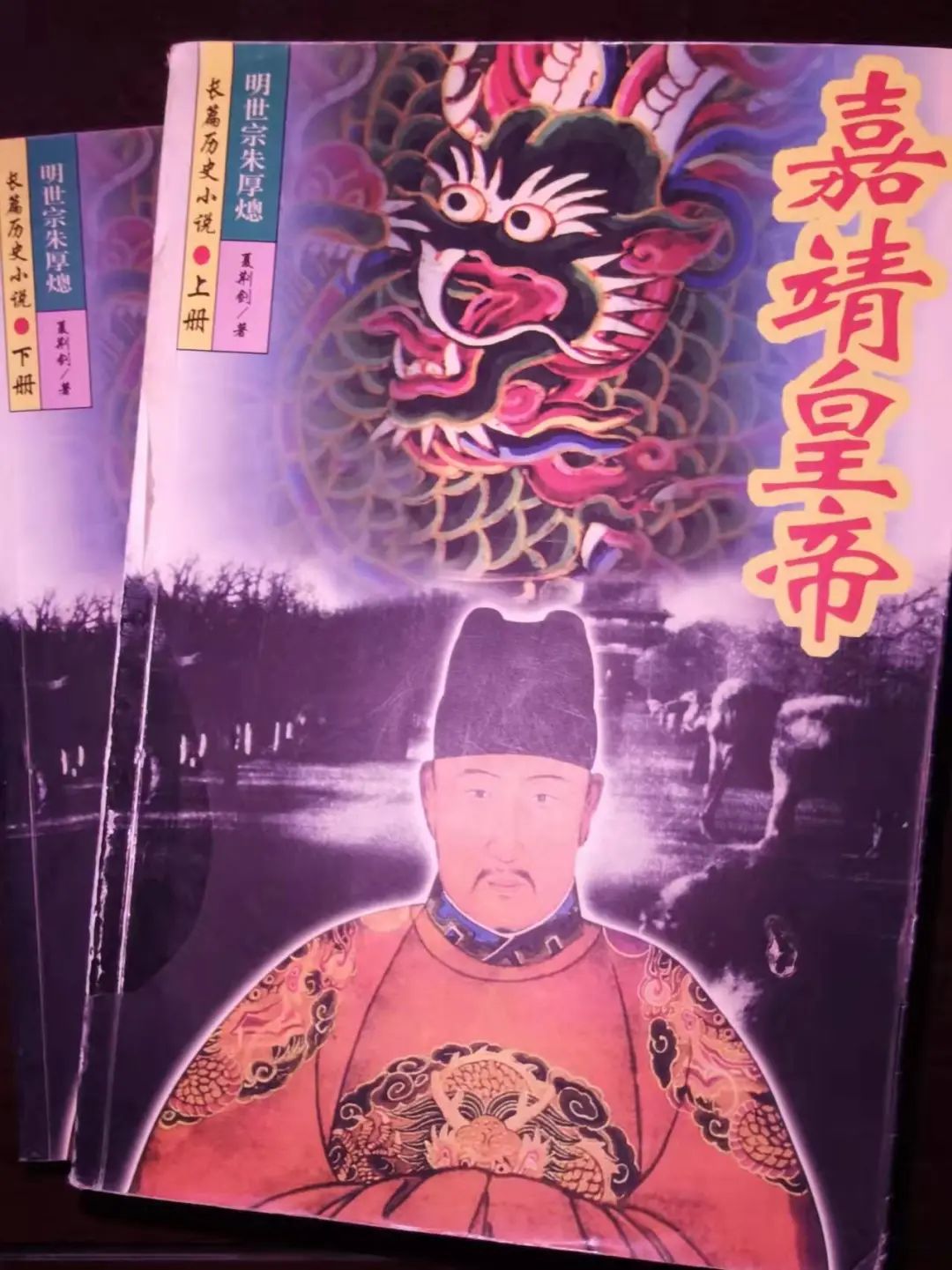
至于這些傳說故事是否確有其事,抑或子烏虛有?那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。倘若真的是查無實據的,起碼也是事出有因的,正如“永嘉場在龍灣,龍灣潭在永嘉”。看似陰差陽錯荒誕不經,仿佛一如真實的謊言,似乎又錯出一段美麗,其實背后也是有因緣所致。
畢竟,“永嘉張孚敬”,張璁張閣老是永嘉人,“三都普門,張璁故里”,張璁張閣老更是貨真價實赫赫有名的永嘉場人。這些,都是鐵板上釘釘的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