耙螺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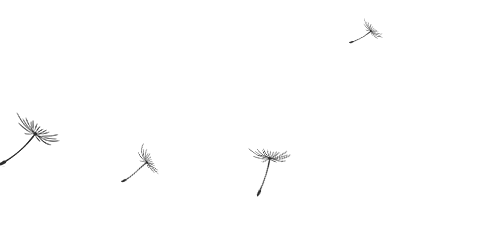
河水清可見底,沿岸綠樹蔥蘢,鸕鶿悠然飛翔,水面木舟蕩漾……這樣的沿河風光定格在老一輩永嘉場人的回憶里。俗語說“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”,農(nóng)閑時節(jié),河邊的人們都會搖著小木舟順著塘河水,或單干,或合伙,耙螺螄來補貼家用。耙來的螺螄有的在船上就銷售一空,有的則運回來,挑出螺螄肉再拿去市場上賣。耙螺螄是那時許多人維持生計的手段,現(xiàn)在成了后人回憶的故鄉(xiāng)舊事。

耙螺螄
文 / 張國棟

歲月不經(jīng)意間已成了故事,少年歲月便是坐在陽臺上,一邊曬著太陽、一邊講與孫輩聽的故事。

小時候家境貧寒,雖然兄妹五人少時都有書可讀,但節(jié)假日為減輕父母的家庭生活負擔,都得干些力所能及的事,諸如:趕涂(撿泥螺、挖白蛤、推“斕鮒丁”、撿扁螺等)、拾柴火(拾糖蔗葉、劈草根、挖糖蔗根、割涂草等)、拾稻穗、捉泥鰍、拔豬草、倒番薯落(就是隊里的番薯地收獲后,個別遺落在地里的小番薯或番薯塊)等等。

上述這些小活還不是我放假期間主要做的活計,我主要活計是耙螺螄,這活不僅要不怕水,而且還要有些力氣,現(xiàn)在我就來講講耙螺螄的故事。
耙螺螄的工具基本是三件套:一樣叫螺螄簞兒,就是在類似且稍大于畚箕狀竹編制的物件中間扎上一根長長的竹竿;另一樣叫螺螄板兒,就是在一塊長方形稍厚的木板中間挖個圓洞套在一根長長的竹竿上;再一樣就是竹簍(永嘉場土話讀音叫籮蛛)。這幾樣物件現(xiàn)在老家已很少看到了,如此敘述寫得挺費勁,然看的人如果沒有用過或見過,其實根本不知所云,還好在萬能的網(wǎng)上找到三張圖,還是直接看圖吧。

▲螺螄簞兒 ▲ 螺螄板兒 ▲籮蛛
耙螺螄是一種體力加一點點技巧的活,左手握住螺螄簞兒上的竹竿把它插進水里直到河底,右手將螺螄板兒上竹竿靠在右手胳臂上,并用食指和中指夾住竹竿,用力把螺螄板兒按下到河底螺螄簞兒前面一點距離,使勁往回拉,這樣將河底的雜七雜八東西耙到螺螄簞兒里,右手拉一下,左手將螺螄簞兒往后挪一下,如此這般五六下,再將螺螄簞兒從水里拿上來,左手抱著螺螄簞兒,右手將里面的螺螄撿出來放在籮蛛里。從水里拿螺螄簞兒時,盡量不要太傾斜,否則耙到螺螄簞兒里的東西就容易掉出來,耙螺螄的整個過程大致如此。

當時耙螺螄的范圍基本覆蓋永嘉場的所有塘河,西至白樓下、河頭龍;北至藍田、山北、上岙;南至三甲,每天基本上會去不同的地方,不過如果一條河里的螺螄多,那么第二天還會再去的。假期里我每天早上8點左右,帶上母親備好的干糧(永嘉場土話“扁兒”),背上三件套出發(fā)去耙螺螄,到了下午4點鐘左右收工回來,中餐就是隨身帶上的干糧,喝的水那是不用帶的,河水便可以喝,中飯就是干糧就著河水。

說耙螺螄要不怕水,那是除水深的時候,人站在河岸上耙外,夏秋兩季水位低時,基本上是要下到河里,站在水深腰部左右的位置。如此,當時我曾感嘆,還是耙螺螄比割涂草舒服,割涂草的場地是在海岸線堤壩外側(cè)的涂灘上,夏天天氣炎熱的時候,渴了根本沒水可喝,而耙螺螄人泡在河水里,別說基本不會渴,就是渴了,探嘴就能喝到河水。

耙回來的螺螄需要將螺螄肉挑出來拿去賣掉補貼家用的,因此每天收工回來后,母親就把螺螄浸泡在水里,讓螺螄盡可能地吐盡肚里的臟東西,凌晨4點多鐘,母親把螺螄燒熟,叫醒熟睡中的我們兄妹5人起來挑螺螄,我們一邊擦著還不想睜開的眼睛,一邊捂住哈欠連連的嘴,極不情愿的起床,由于睡意朦朧,拿在右手的針,會時不時地扎在左手指上。挑完螺螄肉,天剛蒙蒙亮,我便與大妹或二妹,提著螺螄肉沿街叫賣,或賣錢或用大米換均可,7點多無論賣完還是賣不完都得回家,8點左右又得背上三件套去耙螺螄。

初、高中的暑假幾乎沒有休息,整天浸泡在河水里,右手被螺螄板兒的竹竿磨得又紅又腫,火辣辣的痛,然而久而久之右手的臂力倒是比同齡人強了不少。永嘉場的絕大多數(shù)塘河我是相當熟悉,師范畢業(yè)那一年被分到水心王宅的龍灣公社中學,到校報到的第二天去家住朱宅的教導主任朱老師家拜訪,看到他家門前的那一條河,情不自禁地說我曾在這條河里耙過螺螄。
往事如煙,懵懂少年轉(zhuǎn)眼已是退休老兒,歲月成了一個個故事,或心酸或開心。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