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嘉場鮮配亂彈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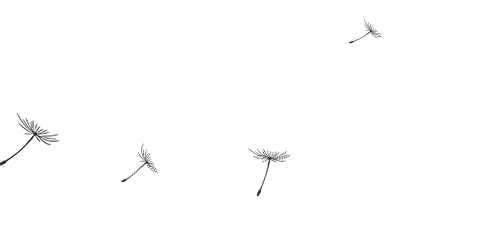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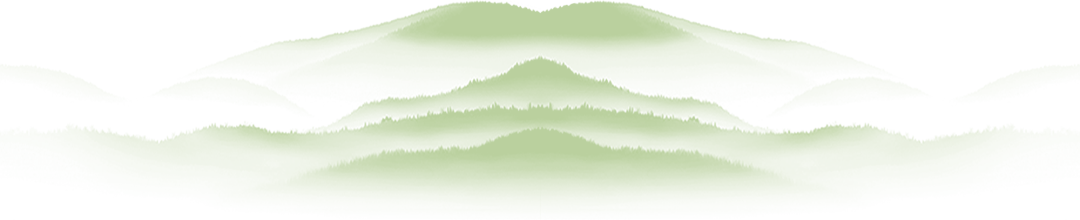
公元前2世紀的西漢初年,永強平原仍是一片汪洋海域,古稱歧海。農耕時代的永嘉場人便以勤奮熱情著稱,他們靠海吃海,種田、打魚、曬鹽。由于超負荷的勞作,這里形成了“一日五餐”的獨特習俗:起床吃“天光”,中午吃“日晝”,下午吃“接力”,傍晚吃“黃昏”,夜晚吃“夜廚”,而海鮮自然成了最重要的食材。各種海魚、蝦、貝類是最常吃的家常菜,不用加太多佐料,海鮮本身的鮮香就足以令人垂涎三尺。雖然,現今許多永嘉場人早已脫離了靠打漁為生的生活狀態,但海鮮仍是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餐桌佳肴。

永嘉場鮮配亂彈
文 / 潘偉光
清順治十八年(1661),永嘉場發生了一個大事件——“遷界”,苛政猛于虎,人禍大如天,逼得本地住戶幾乎“搬光光”。無論天災抑或人禍,“清明上河圖”般繁華的永嘉場都破天荒地成為“千山鳥飛絕,萬徑人蹤滅”的無人區,并且曠日持久災難深重,怎一個“慘”字了得?!家國不幸詩家幸,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,永嘉場的文人紛紛拿起手中的筆,或詩或文傾注了自己的情懷記載了下來。
這里不妨擷取兩位佐證之,張子容不忘故土之思,寫下了“瑤溪曲澗”等十七首吟詠永嘉場景色的詞,李朝賢于遷徙后著《甌江食物志》,以貽后人,“雖鱗介之族繁不止此,即此亦足以見澤國之風味矣。”如果說張子容的《永嘉場十七景》是永嘉場的“景史”(恕筆者杜撰,其實也有道理,即永嘉場地方風景變遷史),那么李朝賢的《甌江食物志》是否可以說就是永嘉場的“海鮮志”。
而之前的王瓚在其編纂的《弘治溫州府志》風俗章中曾說,“其飲食,少芻豢,多重水族”。由此看來,永嘉場人偏食海鮮是有歷史的,迄至今日,龍灣酒店農家樂(人家燒)皆以海鮮為主打菜,如湯臣瑞達、順海悅海、溢香濱海、阿琴昌文三娒奶等等皆如是,所謂一招鮮吃遍天,縱使鰻鲞蝦干之類海鮮干也以“淡甜”為最佳品質。
當然,王瓚文中的“水族”包含了海鮮和河鮮,在當地人的口中還有一個“配”與之對應,意思是說它可以下飯當配,也可以下酒作菜。而永嘉場海鮮中的大佬首推還是黃魚,只因初出水黃如金色,故以為名。腦有石如羊脂,故又名石首。四時皆備,尤盛于春,貴似黃金,故李朝賢評曰:“其利不可以萬計也。”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“打敲罟”高潮,可嘆“孝莊皇后下嫁多爾袞”,已然屈就和掉價。接著王謝堂前燕,飛入尋常百姓家,黃魚遍地,價賤如菜咸一般,家家戶戶配當飯吃。但竭澤而漁之后,黃魚幾乎絕跡,成為永嘉場人的心頭之痛和曇花之夢。
鱸魚,巨口細鱗,味不下松江之鱸。《晉書·張翰傳》里說張翰在洛陽為官,見秋風蕭瑟,想起了故鄉的雉尾莼和四鰓鱸的美味,就棄官回鄉。并寫了一首《秋風歌》曰:“秋風起兮佳景時,松江水兮鱸魚肥。三千里兮家來歸,恨難得兮仰天悲。”張翰之后就在歷朝歷代的詩壇曲苑中,用 “莼鱸”以抒思鄉之情或隱歸之意,于是四鰓鱸和莼菜一起被詩人詞客綴入詩行曲拍,流傳千古。同樣,產于江心嶼和甌江口的子鱭,其味也不下長江刀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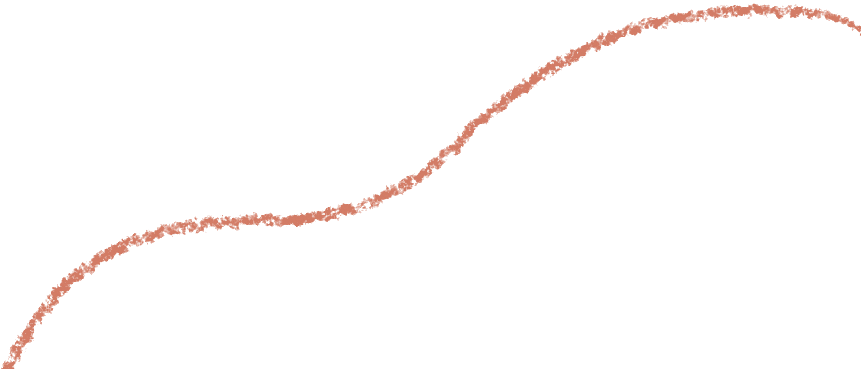

帶魚,長可三四尺,形如白練,與鯧魚并味。鯧魚,形如滿月,無雄,求凡魚為匹,稱為魚中娼。而最有意思是“永強三蟤”(野蟤、沙蟤、泥蟤)和淡菜可以說是海鮮中的情色異類,野蟤,水凍凍的,適宜與水晶糕雜炒,為蟤中最鮮美者也。沙蟤,一般作湯,燒熟后溶解于湯,惟剩下一粒筋皮筋韌的“ 硬核”,有嚼勁,適宜配湯喝;泥蟤類似于“冬蟲”,惜不能化為“夏草”,體內的黃水很臭,所以燒前須擠盡里面的黃水,手法像搓衣,最終而成的“泥蟤凍”可是一道名聞遐邇的地方名菜。淡菜,看外形就概嘆造物主的神奇,鑒于少兒不宜,就不多說了。雖然講得透徹一點,也有加深印象的作用。不過,點到為止的含蓄,可以避免低俗與丑陋。
毋庸諱言,傳統的飲食養生習俗使然,吃啥補啥,以形養形,永嘉場人打心眼里喜歡,這可能歸結為一種表面冷冰冰,里面熱滾滾的“熱水瓶心理”吧!


至于白魚刮鱗,斕鮒刮肚腸,血蛤用嘴咬,那都是永嘉場人掛在嘴邊的笑談。其實有關海鮮詩文、笑話、故事也特別多。如曾在溫州做過官的清郭鐘岳留下了大量的“竹枝詞”,如《蝤蛑》一詩曰:
蝤蛑多肉真堪煮,
田蟢纖螯未可持。
勸學豈徒攻爾雅,
莫教誤食當蟛蜞。

毋庸置疑,海涂上的爬行動物十只腳帶殼的,除了蝤蛑是老大外,還有駝背凸凸,但見一邊爬一邊嘴里吐泡泡,外形像松葉蟹帝王蟹的遠房親戚,也仿佛縮微版的后裔曾孫輩。還有,鄉人蔑稱的“拉尿蟹兒”,試問有誰看到過它撒尿的樣子。大鰲穴,如陳真師父獨臂老人,平常挺著一只大鰲,行走江湖。毛蟹,長得規規矩矩長長方方,和田嬉兒似有血緣關系,屬于腿上長毛的毛孩異類。青蛄,跟拉尿蟹兒長相頗像,一月青蛄二月蟹,三月青蛄扔茅坑……草繩系在蝤蛑上,與蝤蛑等價;竹爿嵌在鰻鲞里,和鰻鲞同值;人跟人隊銀跟銀隊,跟牢冇好伴一世給狗管,可見站位多重要。跟著狼,千里有肉吃, 隨著狗,十步必吃屎,除了那些吃屎不忘拉屎人的腦殘傻逼神經病。這難道是永嘉場人多年以來吃海鮮形成的價值觀乎?
又如海鮮故事傳說,如“蝦蛄與水饞”。水饞,水靈靈、糯糯動,饞得人們口水往下掉,聽打漁人說剛出水的還會叫。小時候的我們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景,大人看到掛著鼻涕的小孩,往往會說快回家叫你媽把它摘下來給你雜粉干吃,時隔多年以后想起,仍然忍俊不禁,夢中都會發出笑聲。我想這大概是水饞又叫“鼻涕魚”的由來吧,非常生動形象!蝦蛄,永強人稱它“蝦蛄彈”,特地在蝦蛄后加了個“彈”,警示吃它的時候要小心,弄不好會劃破嘴巴或舌頭,吃相難看。在永強民間傳說中,蝦蛄屬于“道德品質差”的異類,如它騙取了“龍頭魚”的官帽盔甲。平生不做虧心事,半夜敲門渾不怕。所以,蝦蛄一見龍頭魚就“鬼見愁”,全身縮卷成一團,而龍頭魚仇人相見分外眼紅,張開血盆大口,一口就將其“內卷”了。“龍頭魚”又習稱“水饞”或“水魚”,水魚吞殺蝦蛄的傳說,也可視為“柔弱勝剛強”的一個注腳。后來,在永強人傳說中,杜撰一個“張閣老進獻蝦蛄給嘉靖”的橋段,為的是讓真正的“龍口”品嘗一下蝦蛄這魔鬼魚的味道,最好能成為貢品,讓蝦蛄家族世世代代為奴,遭受從永強到京城的顛簸流離之苦,以示品德敗壞之懲戒。
又如鰻家族,有河鰻、江鰻、海鰻,狀皆如蛇。鱔魚,又如河鰻,泥鰍次之,皆于田中得之。它們的共同特點是滑頭滑腦手難以握牢,不過民間傳聞都是滋陰補陽的,所以也受食客們喜愛。于是,大朵快頤之間,笑話隨口而出——話說烏龜追河鰻,河鰻進洞泥鰍出來。烏龜大怒,揪住泥鰍一頓罵曰:“你爸呢?男子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,自己躲起來作縮頭烏龜,卻推三歲小孩出來當擋箭牌,虎毒不食子。這龜兒子,真TMD-TNND!”
蝦蟣蒸肉、野蒜炒糕、番人芋燒球菜……諸如此類的菜名,有時也讓人大跌眼鏡,聽得人一頭霧水,蝦蟣、野蒜、番人芋有這么大的能耐,不會吧?!倘若有,也不過是打獵人憑狗的勢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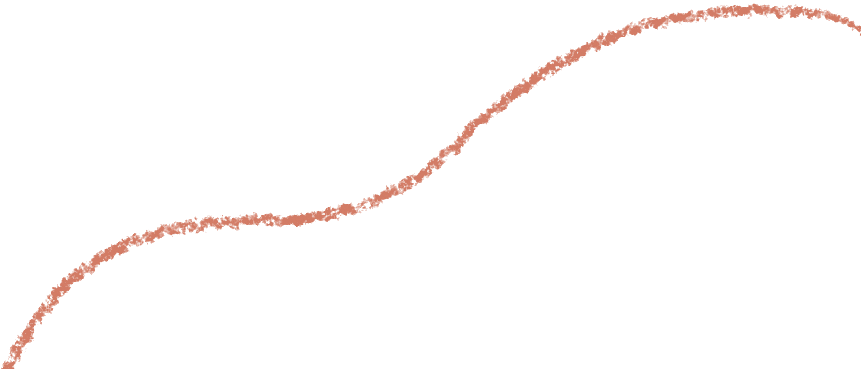

李朝賢曾在《甌江食物志》里也提到過低檔次大路貨的海鮮河鮮,“烏鯉、八須、馬鮫,亦有食之者,鄙不足貴。君魚、王魚、火魚,又次之。虹魚腥甚,最賤,成鲞更名鐵”。不過,時下烏鯉八須都被酸菜水煮了,王魚綁上狀元,弄得霸氣十足,讓張智番茄西瓜諸酒家也火了一把。像爛頭鰲兒此類弱勢悲情的小小魚,還是有待提升炒作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,風水輪流轉,君不見泥鰍已趕超河鰻了。
海蜇應該是最富有哲理的一種海鮮吧,海蜇,永強人叫藏魚,顧名思義,你可以藏起來慢慢享受,吃它個天長地久。也有人把它寫作“臟魚”,其在水中游姿猶如心臟等人體臟器的搏動。其實海蜇廣泛被人接受的名字叫“水母”,因水母和蝦共生雙贏,故舊時鄉間有“蝦兒當眼”的戲語,水母原來目是蝦,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水葫蘆,但經礬后,圓滾滾的球體變成了一個扁欣欣的平面圓,惟剩下一張近乎透明的皮,它似乎又在告誡警示人們——幾十斤乃至上百斤的海蜇擠干水分后,沒有幾斤幾兩,用不著到處吹噓自己厲害!海蜇花,每個海蜇有四朵,特別鮮美,永強人叫藏紅花。莫非永強與西藏歷史上也有什么千絲萬縷的關系?待考,歷史深不可測如古井,上面清冽可口兮,下面泥沙混雜,里面有沒有珍珠寶貝,需要反復淘,淘盡泥沙始見金。

如今疫情沒完沒了,餐飲亦難作!你方唱罷我登場,各領風騷沒幾年,幾年前五溪沙人家燒火爆,沿路停滿了各色車輛,家家客滿,來晚了定個包廂都難!不料短短幾年,紛紛關門倒閉,盡管路好了,就餐環境也改善了,就是鐘馗爺開飯店,鬼也不見一個。如今,只剩下這家以五溪沙命名的人家燒,在凄風苦雨中硬撐著,夠堅強!











